杨博文评《铸典宣化》|国际体系何以塑造清末民初宪制
- 国际
- 2025-01-25 10:46:07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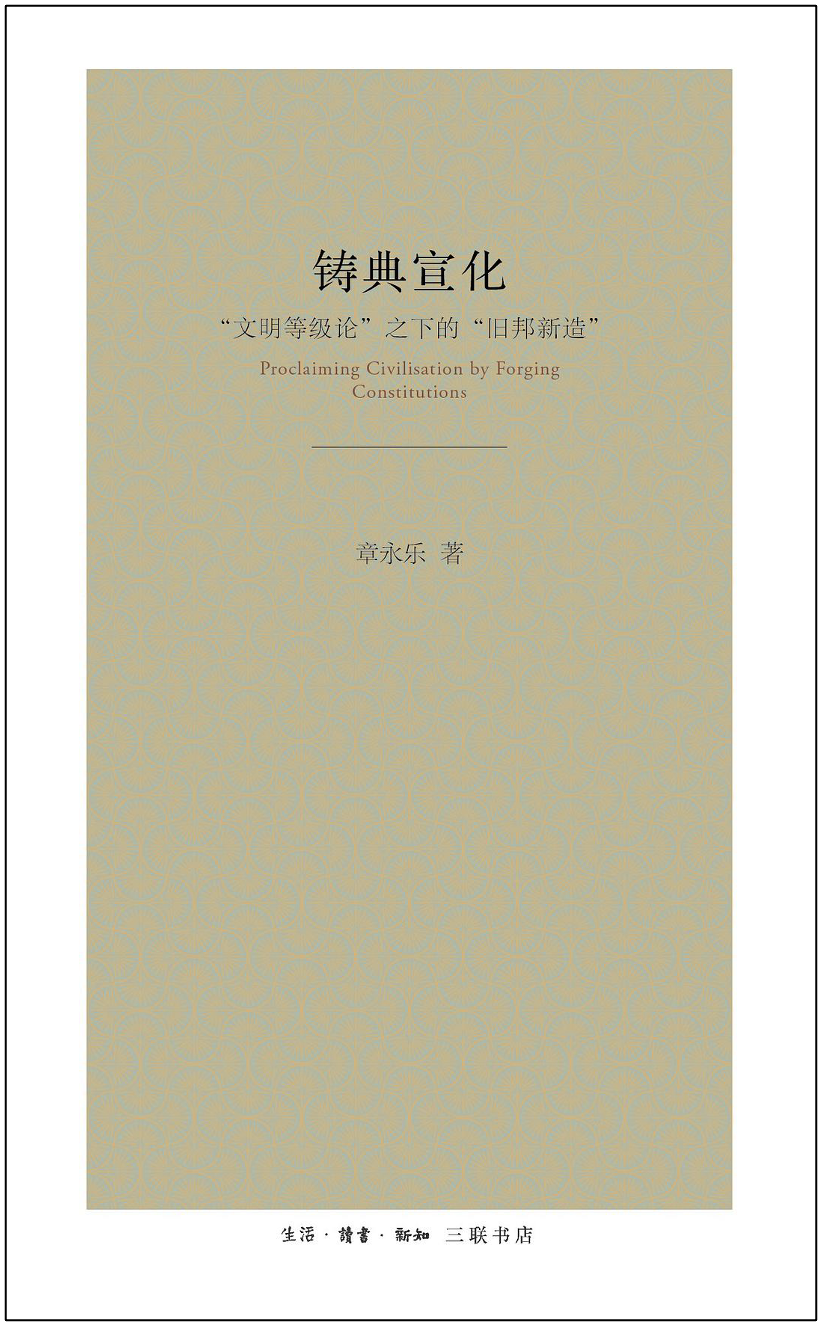
《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章永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0月出版,284页,69.00元
1906年8月26日,端方在向慈禧太后进呈的《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中力倡“立宪”,认为日本战胜沙俄的关键在于前者制定了成文宪法:“此立宪与否之原因,即为兵强国富与否之原因,可以确见而无容疑义者也。”端方进而指出,清王朝若想富国强兵,必须制定成文宪法,采用立宪政体。达寿在1908年8月进呈的《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中进一步阐发了端方“立宪可以固国体”的主张,认为不立宪,则无法在军事、财富、教育三方面提升国家竞争力,“竞争力不厚,则不足以立于国际竞争之场”(126-137页)。

五大臣出洋考察合影
武备充沛、国库充盈、民心凝聚——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包括历代“变法”经验中,并不缺乏能实现这三项目标的治理工具,处在“封建君主专制顶峰”的清王朝对此一定不陌生。但为什么此时的清廷会选择立宪(制定成文宪法)来实现上述目标呢?我们当然可以诉诸“成文宪法的优越性”。自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以来,新兴独立国家的建国精英大多以成文宪法形式来阐明其国家治理的总体制度设计,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的明晰易懂:成文书写的形式将那些教义公开化,以往高高在上的根本法原则开始被广大公民知晓和辨认。在此意义上,成文宪法也被视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建构主义的胜利”(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清华法学》2016年第三期)。
《铸典宣化》一书将答案指向国际体系。作者认为,之所以清政府选择立宪(制定成文宪法),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下,制定成文宪法是后发国家实现富国强兵、进入“列强俱乐部”的常用做法,德国、日本均取得了这一意义上的成功。本书的主线正是维也纳体系及其变动对国内宪法秩序的深刻影响:在维也纳体系尚存时,国内各政治派别的行动都会寻求体系内主导国家的支持;当德国、日本等国从体系边缘“跃迁”至体系中心,它们的宪法实践也会被中国借鉴;当维也纳体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解,国内的宪法讨论议题相应地发生了重组。作者反复提到“一战”对国内宪法观念与宪法实践的冲击——如果不满足于一种庸俗的“战争决定论”或“军事决定论”,那么就必须将“一战”理解为维也纳体系作为一种主导性国际体系的崩溃,进而探讨国际体系如何塑造国内的宪法秩序。
国际体系对国内宪制的塑造,是作者一直以来的核心关切。2011年的《旧邦新造:1911-1917》就已经探讨了辛亥革命以及民初宪法斗争所处的国际环境,指出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得以保全的原因包括觊觎中国的列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定均势。不过此时作者尚未将“内外关系”视角充分展开,这一视角的初步成熟是在2017年的《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中,作者以康有为为考察样本,细致梳理了维也纳体系的变动对于康有为宪法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在2021年的《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一书中,作者对“内外关系”视角的运用臻于完善,“空间政治”概念的引入让国际体系塑造国内宪制的研究更为理论化。2024年的《铸典宣化》,是作者将已经运用成熟的“内外关系”视角作了更为充分的展开,本书的余论部分也强调了若干著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还提到书中“二十世纪之宪法”的部分直接受到了汪晖《世纪的诞生》一书的启发。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国际体系塑造国内宪制”为线索,尝试串联作者近年来的若干著作以及汪晖的两部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国际体系对国内宪制的“塑造机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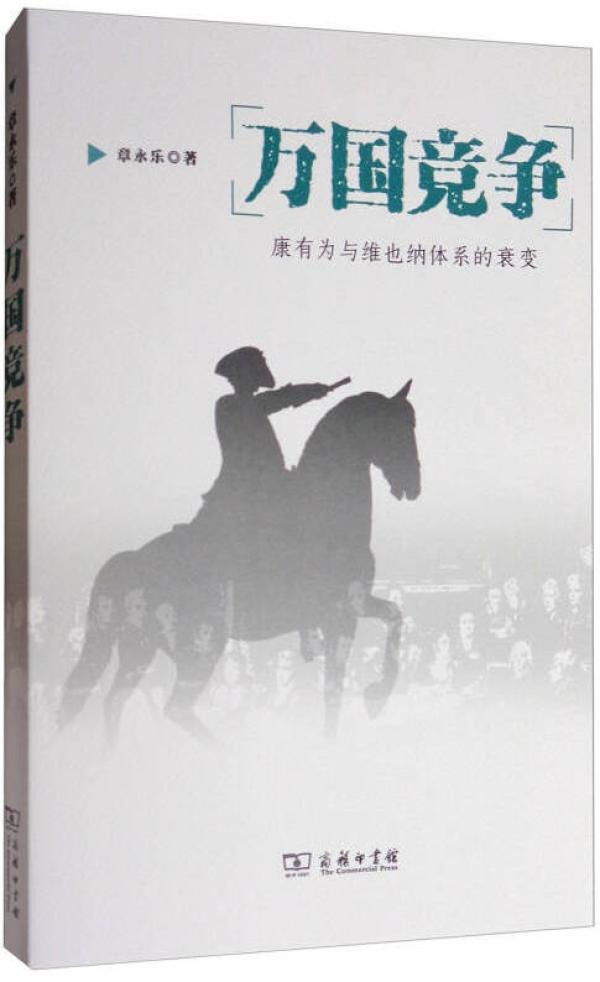
章永乐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文明等级、“时间化的空间政治”与维也纳体系
机制解释在实证研究中并不陌生,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经常关注国际环境对一国内部政治转型的影响。例如,斯考切波关注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对威权国家内部革命性危机的激发作用(《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3-24页)。迈克尔·曼分析了全球资本作为一种“弥散性权力”,如何对一国内部工人抵抗运动进行“包围”(《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11页)。更多学者关注了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之间的“示范效应”,国家间的学习与竞争、霸权国的推动、价值观传播等因素也会影响一国内部的宪制演变(胡鹏:《国际环境、政治精英与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政体的兴衰》,《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上述影响因素或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空间革命”。海洋时代伴随着工业和机械的力量,空间的拓展重构了国际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秩序,带动着城乡关系、国家形式、地缘关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重组。随之产生一种“概念横移”现象,即“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45-46页)。诸如“门罗主义”“民主”“民权”“主权”等诞生于西方的话语和概念得到了“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待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这一原属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概念被挪用到了二十世纪中国。《铸典宣化》详细梳理了“文明”一词如何进入晚清至民初的宪法讨论中,这也是维也纳体系影响近代中国宪制演变的主要体现。晚清的政治精英注意到,新兴独立国家主动接受“文明”话语,通过自我改造进入文明国家行列,这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普遍现象。国内精英对于“文明等级论”有一个较为曲折的接受过程。在观察到日本和奥斯曼帝国的正反例子后,他们开始将“立宪”与“文明”相关联。国内政治精英经过一系列的外部观察得出结论,制定成文宪法可以跻身文明国家行列,甚至进入“列强俱乐部”(22-27页)。
“文明等级论”是一种“时间化的空间政治”。作者在《此疆尔界》中追溯了“空间政治”的生成机理,它产生于持有歧见的不同群体对空间的“对象化和客体化”,并围绕空间边界的分歧和冲突达到一定强度,“门罗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政治”。相比于“门罗主义”,“文明等级论”不仅包含空间因素,也包含时间因素,它将空间置于“从属于时间的位置”,假定人类历史是一个“按照不同阶段渐次发展的过程”,而同一时间处于不同空间、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就可以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被置于时间线的不同位置”。在十九世纪,欧洲相对于其他区域发展得更为完善,在文明等级体系下也就有了某种“领导乃至支配其他区域的资格”,欧洲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支配也被解释为“站在先进的历史-时间位置教化万邦的伟业”(《此疆尔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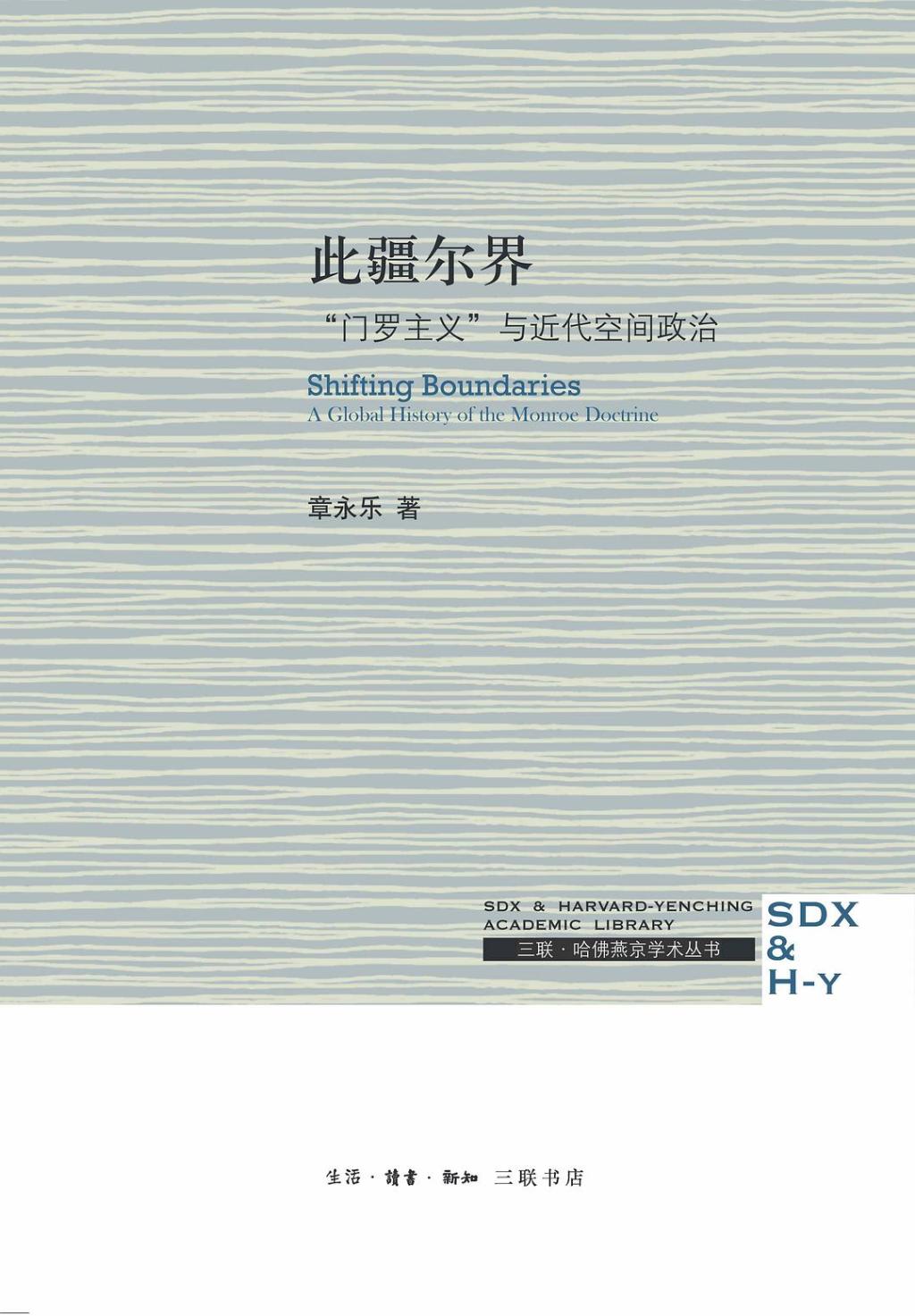
章永乐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如果说“空间革命”会引发概念移植,那么叠加了“时间革命”的“空间革命”,即“时间化的空间政治”则会引发概念移植中的“扭曲”。《此疆尔界》就详细梳理了“门罗主义”一词在诞生后的“扭曲史”,不同政治主体对于同一词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解读。《铸典宣化》则梳理了“文明”概念被移植到中国后的类似现象。例如,辜鸿铭在反对晚近以来西方“尚智与力”的文明观的同时,指出“中国文明”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甚至可以拯救西方的文明;“一战”前后,“文明”观念在国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战后开始出现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毛泽东提出了“复数”的文明观,不再认为某一种单独的“文明”是普世标准(165-220页)。
如何理解“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国宪制演变中的“扭曲”?作者在《此疆尔界》中提醒我们,如果某一概念在后世的运用中与“原版”不同,并不一定是运用者别有用心、缺乏理解力甚或“良心败坏”——“从历史经验来看,立足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事物作为行动的资源加以应用,本来就是人类行动的常态”。我们作为历史经验的研究者,有义务去解释这种距离何以出现,“追踪这个词语的意义流变,来探究政治社会发生的运动”(19-20页)。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常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大多源自“对十九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但都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从而用于新的具体政治实践中。每一次重复也是“置换”,旧概念的新用法,看似是对概念的误用和错误移植,实际上“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世纪的诞生》,43-44页)。

汪晖著《世纪的诞生》
国内政治精英对“文明等级论”的接受,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客观的国际等级划分方法,而是一个主动的事件,是“通过对独特时势的把握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方向的主体行为”(《世纪的诞生》,16页)。而“文明”概念在接受之后又被抛弃、被改造,表明精英们对时局的判断发生了改变。在“一战”爆发之初,国内的宪法讨论仍然限于“文明等级论”。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文明等级论”在国内舆论场上发生了变化。杜亚泉在“一战”前是国家主义和“天演论”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在见证了“一战”中各“文明国家”的野蛮厮杀,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他开始系统反思西方的文明观念。“一战”结束后,通过“立宪”跻身文明国家行列的做法被广泛质疑。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步占据了“文明等级论”的“生态位”。普遍历史的衡量尺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内精英开始深入思考宪法演变中的普遍性因素(192-262页)。
“新旧分化”与“志趣转移”:政治精英作为国际体系塑造国内宪制的“中间环节”
文明等级,仅仅是国际体系的表征。若要将各个国家都整合进一个国际等级秩序中,也就是说,“文明等级论”要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国内部的政治精英主动接受并实践这一理论。在此意义上,政治精英构成国际体系塑造国内宪制的“中间环节”。而由前文可知,国内政治精英基于对特定局势的判断,主动接受、抛弃和改造了“文明”概念。这表明作为“中间环节”的国内政治精英具有高度能动性,他们并非单方面接受国际体系的灌输或塑造,而是像一个巨大的“筛子”,国际层面的要素在经过政治精英的筛取、过滤后进入国内层面,实现国际体系对国内宪制的塑造。
那么,这个“筛子”或“中间环节”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涉及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的精英主义范式,宪法学者对此也有所阐发。理查德·凯(Richard Kay)将现代成文宪法视为“特定社会中的精英围绕重要利益进行谈判的结果”。霍夫曼-朗格(Hoffmann-Lange)认为,成文宪法的制定并不反映全民的共同利益,而是精英“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一愿望的体现。赫克托·波菲尔(Hèctor López Bofill)更加尖锐地指出,宪法既非人民行使制宪权的产物,也非各方签订的社会契约,而是“暴力的结果”,是获得胜利的精英团体对其强制统治的法律转化(Bofill, Law, Violence and Constituent Power: The Law,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Constitution Making, Routledge, 2021, pp. 42-78)。作者早在《旧邦新造》一书中就关注了政治精英在清末民初宪制演变中的作用,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党人这两大政治精英群体的共识与分裂,决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命运和民初政局的维系与破裂。《铸典宣化》并未有意延续这种精英主义范式,但我们可以从作者梳理的大量现象中归纳出政治精英作为“中间环节”的两种运作机制,即“共识分化”与“志趣转移”。

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
(一)“新旧分化”
精英主义范式本就强调“新与旧”的对立。该范式的奠基人帕累托基于“生理学定律”,将人类历史悲观地概括为“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其中,新一代精英会“充当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宣称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不是一个有限阶级的权利,而是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4页)。
在国际体系发生剧变时,围绕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分歧,一国内部的政治精英会极速分化出新旧两个群体。旧政治精英倾向于在原有国际体系下思考国家出路和宪制安排。例如,晚清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精英曾试图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以保全自身完整性,但维也纳体系尚在维系之时,列强间的共同利益远盖过其内部矛盾,它们通过“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网络”“六国银行团”等大国协调机制挫败了国内旧精英的“以夷制夷”企图。更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他坚信君主立宪制是维也纳体系下列强的主流宪法实践,因而直到1920年代还试图“策反”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溥仪复辟。康有为作为旧精英的“短视”还体现在对新兴反霸权力量的忽视。他在欧洲和德国考察期间看到了德国通过立宪实现富强,但也忽略了德国的劳资纠纷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政治精英开始摆脱对旧国际体系的依附,并寻求新的力量来源。《铸典宣化》追溯了“一战”期间李大钊、茅盾等人的思想转变,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可以作为超越东西方文明的“第三文明”。即便是“一战”后并未对西方文明产生幻灭感的胡适,也注意到了美国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168-215页)。
新旧精英围绕国际体系存在认知分歧的同时也存在一点共性:无论是旧精英关注德国、日本,还是新精英推崇美国、俄国,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识别出了维也纳体系作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薄弱环节”。本书作者曾在2023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作为维也纳体系下“大国协调”的客体,最终成为全球少有的通过“旧邦新造”摆脱客体地位的国家,“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是重要条件(《“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国际层面的非均衡性传导至次一级的“政治空间”,就形成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彼此互动的“薄弱环节”,即“列强争夺国际势力范围的进程与其对中国境内瓜分势力范围的进程相互伴随”。但“薄弱环节”并不是一经生成便自动引发革命,它“从潜能变为现实”需要新一代政治精英主动将其识别出来,尤其要将两个空间层次的“薄弱环节”结合起来考虑。识别出新的时势,进而主动寻求制胜的战略、策略——新的政治主体在此过程中持续生成(《世纪的诞生》,30-32页,81-82页)。新一代政治精英逐步摆脱国际体系依附、寻找新的力量来源,这是建构或自我建构出新政治主体的关键一步。
(二)“志趣转移”
《铸典宣化》着重描绘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在“一战”爆发后,国内政治精英的“兴趣点”发生了集体性的转向。首先,有相当多的政治精英对宪法的兴趣减弱,转而对社会经济问题抱有更大兴趣。这一时期,国内的宪法讨论议程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政争核心的“法统”问题不再被各方关注(227-255页)。杜亚泉批评了以成文宪法和议会政党竞争为表现形态的“政治主义”“十九世纪政治”,反思了各政党为追求一己私利而恶性竞争、引入外力造成的民初政治乱局。在此基础上,杜亚泉将关注重点转移至“二十世纪政治”“经济之政治”,关注因战争导致国际产业链断裂的问题,注意到“一战”的爆发与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密切相关(194-199页)。梁启超早年间深度介入清末立宪,并以进步党和研究系领导人的身份进入民初议会政治,但在“一战”结束后,梁启超极少关心宪法和法律议题,彻底转向社会经济领域,深耕国民教育。他创办的“司法储才馆”作为法官培训班,却在课程表中大量设置社会学、人口学课程(李在全:《梁启超与司法储才馆》,《历史研究》2020年第五期)。很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都高度关注宪法议题,新文化运动正发端于对“假共和”和袁世凯变更国体的抨击。毛泽东早年曾深度参与湖南省宪法草案的讨论。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集中发表过一批宪法文章,涵盖省制、思想自由、弹劾、议员薪俸、宪法公布权、两院制等经典宪法主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在“一战”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关注重点,从宪法领域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即便是仍然关注宪法的政治精英,其关注的具体宪法议题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宪法讨论者从宪法传统的议会政党和政治权利议题转移到了社会经济权利中。“一战”结束后,作为“现代宪法奠基”的《魏玛宪法》成为国内宪法学人的“宠儿”。192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围绕《魏玛宪法》的“生计制度”展开。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由“二十世纪之宪法”这一概念进入国内宪法讨论中。此外,宪法的内容(“宪法应当规定什么”)的关注度开始让位于“实质宪法”(宪法的制定主体是谁),宪法讨论者开始从社会革命中寻找成文宪法的存立基础(231-265页)。国内政治精英在“一战”后对于宪法和政治的认识更加成熟,认识到“政治乃事务执行之机关,而非质力发生之产地,必民力充韧,百务振兴,而后政治乃有所凭藉”,从而将“政治”置于日常生活的深厚基础之上(《世纪的诞生》,248页)。
如果某一时期,大量社会精英的职业兴趣或关注重点都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这就构成一种值得关注、有待解释的现象,可以将之概括为“职业兴趣转移”或“志趣转移”。在此方面,罗伯特·默顿做出了典范性的研究。默顿注意到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社会精英中出现了一种“不成比例的、对科学的明显兴趣”,出现了明显的从神学到科学的“职业兴趣转移”,而“清教主义”作为当时一种“强大的、不容轻易反对的社会力量”,构成这种转向的文化-价值基础。在“清教主义”看来,除了“赞颂上帝”这样一条“不受挑战的公理”外,所有的概念、理论、见解都要受到经验的检验——这与近代科学如出一辙,后者也认同一种基础性假设,即“存在着一种事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界的秩序”。除了这一条之外,所有的科学猜想都需要经过经验性的实验加以证明,在此基础上才能用各种逻辑工具加以提炼。清教主义和近代科学观念都存在那种“不受质疑的基础性假设,以它为基础,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而建立起来了”([美]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101-152页)。

罗伯特·默顿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可以看到,“清教主义”促成“职业兴趣转移”的关键在于它颠倒了逻辑-经验关系:“对实在的检验”不再来自“学究的逻辑”,而是来自对经验事实的观察,这构成“清教主义”和近代科学的共同特征;强调“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而逻辑“被降低到从属的地位”(同前,107-108页)。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存在类似的“颠倒”现象。汪晖指出,晚清至“五四”的国内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认知范式转变,“天理”作为“前西方”时代中国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经历了解体,结果是“公理”/科学世界观的产生。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在于“理”与“物”的关系:“天理世界观”把各种物质或利益关系看成是一种道德的、心性的、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而用一种道德知识(比如理学、经学、史学)去理解这些现实关系,而“公理世界观”把伦理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物质的、利益的、必然的关系,进而用实证性、经验性的自然或社会科学知识来“去除这些关系的神秘性质”,试图按照事实的逻辑或自然的法则建构伦理和政治的根据。“公理世界观”在激烈批判“天理世界观”的同时,也把“理”这一代表着超越时空的普遍秩序的概念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还是“公理战胜强权”“文明战胜野蛮”中的“公理”“文明”,都保留了某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它们都将某种超越性的“理”理解为最终的、普遍的价值,进而剥夺这个“理”与现实秩序的人为联系,揭露这个现实秩序的反“理”的特质。那么,只要存在“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这种世界观就会不断发生危机和自我瓦解(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7-68页)。

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战”结束后,《魏玛宪法》作为一个“战败国”制定的宪法能够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普遍青睐,因为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明等级论”不再主导他们的认知——“公理世界观”在战胜“天理世界观”之后,自身也面临崩塌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一开始寄希望于模仿先进国家的立宪经验实现富强,在现实政治中受挫后,转而放弃“纸面”上的宪法或“制度救国”方案,“下沉”到更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这种转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有实用理性传统”或“缺乏宪政文化土壤”,这背后有更为深刻的世界观/认知范式转变的线索值得挖掘。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然后呢?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本书做一点总结。某一时期的国际体系可以呈现为一种等级秩序(“空间的时间化”),经由政治精英这一“中间环节”实现对一国内部宪制的塑造。但国内政治精英并非被动地接受塑造,而是会有选择性地筛取、过滤国际体系中的因素。他们在面对国际体系时会发生“新旧分化”和“志趣转移”现象,在此过程中将外部因素转化为国内宪制的塑造力量。
然而读者不难看出这段总结的问题,这里并未出现“文明”“立宪”“二十世纪之宪法”等《铸典宣化》中的关键信息。换句话说,即便抛开这本书,也不影响上述论断的成立。这也是本文与作者可能存在的一些方法上的差异。作者在本书中延续了《此疆尔界》以来的概念史方法,将“文明”等概念视为“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分析这些概念在传播过程中的起源、断裂和变形,观察其背后发生的现实政治斗争(《此疆尔界》,19-20页)。作者对这些概念在不同场景下的具体用法做了十分细致的搜集和分类,但史料的扎实与“理论性”往往无法兼顾。“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清末学人对“明治宪法”的激烈争论、“二十世纪之宪法”概念在“一战”后的突然发酵——这些故事固然精彩,但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复原了这些话语现象背后复杂、激烈的各方斗争,对一些我们过去一直深信不疑的政治观念做了祛魅,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本书结尾给出了作者的当下现实关切,提出我们国家应当适应从“应试者”到“出题者”的角色转变,力倡“自成体系、自建光荣”,其论断依据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国际体系与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体系相似,都面临剧烈变动的情况(265-268页)。作者在这里引用了电影《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基于历史经验的观察来回应现实关切,这其实包含一项“预测”工作,而“预测”是需要理论的,需要在观察“彼时彼刻”的基础上提炼出若干机制,识别出是否存在类似场景的复现、在多大程度上复现,再根据相似程度调整、适用、改进已提炼的理论,将之转化为“此时此刻”的行动力量。
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理论野心”的缺失,这也是“主位”(emic)与“客位”(etic)研究的差异使然。作者曾在《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一文中区分了两种研究类型:“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世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把握历史行动者自己所具有的规范观念的具体实践意涵,并追问这些具体规范观念所预设的前提,而“客位”研究是指研究者将当代的观念和分类体系,而非历史行动者的语言直接用于历史描述和历史评价。作者的研究可以归入到“主位”范畴,而从历史材料中提炼理论或若干机制并扩展运用,无疑是用后人眼光审视前人的“客位”研究。不过两种研究立场并不矛盾,理论的创新需要以扎实的材料为基础,站在后人的研究视角上对前人留下的零散素材做系统的归纳,在细致地还原语境之后再去探讨更为普遍的理论问题——这或许是本书对于当下众多“客位”研究的最大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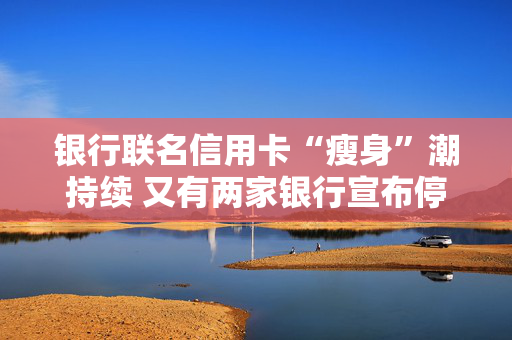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