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物质?谁是我?整形、科技与身份:2025金球奖电影启示录
- 汽车
- 2025-01-25 12:06:08
- 21
2025年1月5日,第82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获奖名单揭晓,作为2025年第一份国际级电影获奖名单,金球奖不仅是奥斯卡前哨站,也对2025年的电影内容表达具有风向标意义。对比去年的获奖电影,2025年金球奖可谓2024年“升级版”。2024年奥斯卡两大赢家《奥本海默》和《可怜的东西》分别关于科学天才和女性,今年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粗野派》关于建筑天才;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女主、男主的《艾米雷亚·佩雷斯》、《某种物质》、《不同的男人》及获5项提名的《阿诺拉》,则从单一女性话题,扩展到女性、男性和两性维度,涉及整形和身体话题,置于科技语境下,带有科幻、恐怖与超现实主义色彩。
两部邪典惊悚片《不同的男人》与《某种物质》可谓“互文”,是男女版本的人类/怪物、自我/他者二元式电影。《某种物质》的女性在男性凝视的世界里,通过整容获得“更好的自我”,无论是分离出的美丽尤物,还是为供养年轻美女而被榨干成丑陋物质的女主,都是人被物化;《不同的男人》讲身处社会审美规范的男性遭遇容貌歧视,通过整容手术变成“更英俊的自我”,但无论是患皮肤病的自己,还是英俊的自己,都只是为符合剧本角色而存在的物质,也是物化后的人类。外在身体特征变化引发的内在身份认同危机,也出现在《艾米雷亚·佩雷斯》中,整形不仅改变容貌,也改变角色,厌倦男性杀戮世界的黑帮头目,既渴望成为女人获得安宁,又保持异性恋性取向,在“过去的男人”和“现在的女人”两种身份间游走,时而合二为一,也是个“不同的男人”,《阿诺拉》涉及的性工作者也围绕身体主题展开。
人类的物化与异化,出路何在?2025年金球奖的答案是悲观的。《不同的男人》与《某种物质》表现的“平庸之恶”,没有反抗物化,却在自我物化上走得更远,成为物化的合谋和帮凶,《艾米雷亚·佩雷斯》和《阿诺拉》亦无法走出社会框架,成为牺牲品。而人类物化背后,是更大的议题——科技,企图用科技投射欲望的人类,被科技反噬,才最可怜。
生成式人类,谁是更可怜的物质?
《某种物质》、《不同的男人》和《艾米雷亚·佩雷斯》,与去年获奖电影《可怜的东西》异曲同工,都涉及母体生成(Generative Matrix),即一个可生成、可再生的母体分离出或蜕变成一个新的子体,如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无论母体与子体是在同一身体上,还是不同身体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又因通过非自然分娩的科技,成了似人非人的“物质”(Substance)或“东西”(Thing)。电影的焦点,在于如何面对自我的两面性,即如何与自我相处,和处理两个自我的关系。

《某种物质》(左)与《不同的男人》(右)
《某种物质》从衰老母体的背脊分离出子体,构成一对存在于两个身体上的母女,一个是曾经不好的自己,一个是现在更好的自己。《可怜的东西》将母亲遗体胎盘中的女婴大脑移植到母亲遗体上,形成一个母女共生的身体,如同创造这个“东西”(Things)的古德(God)所说:“她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女儿”,是成年女性身体与女童大脑的拼接。

《某种物质》中“母女”伊丽莎白与苏

《可怜的东西》中的“母女”维多利亚与贝拉
《可怜的东西》中的“东西”贝拉,被当做实验室生物对待,通过婴儿智商与成熟身体的错位,形成对身体的全新使用方式。“女儿”贝拉对身体极具自主意识,与“母亲”维多利亚遭遇的压迫形成对比,在无意识的、错位的身体支配下,造成对秩序的反向抗争,也变相救赎了母体。物质般的“东西”反倒更有人性,并不可怜,身边企图支配控制她的人,才是“可怜的东西”。
相比而言,《某种物质》的自我关系“更可怜”。年轻美丽的“女儿”苏(Sue),对“母体”伊丽莎白不仅厌恶,还对其剥削。苏对女主的剥削,其实是女主自己对自己的剥削,这种自我剥削,比以娱乐公司老板为代表的外部剥削,更残酷恐怖。苏每增加一分美丽,伊丽莎白就被消耗一分健康。伊丽莎白逐渐干瘪的躯体,就是苏剥削行为的记录和证据。苏的成功,是欲望、贪婪和践踏他人的累积。她外表愈美,内在愈丑,诚如现实中很多表面光鲜的人,内在实则龌龊肮脏。导演用更直观的丑陋物质,将抽象的邪恶内心,变得可视化和证据化,像极了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是自作自受,并不“可怜”。她被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无节制的贪婪;她对苏的供养,是有目的地把苏当工具,以满足自私欲望;她也并非单方面被剥削,出于嫉妒,她也主动给苏搞破坏。伊丽莎白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不断打压自我,不能善待自己,没有自我认同和自爱,只依赖外界的虚假之爱,就会为追求名利成功,而泯灭自我良知与善良,变成行尸走肉,可谓自食其果。诚如电影中的一位同样吃过“神药”的老年男子对伊丽莎白说:“你是不是更孤独了?她有没有把你整个吞噬掉?你只为证明你存在的价值罢了。”
谁是不同的男人?
《不同的男人》里,究竟谁才是不同的男人?三个显而易见的“不同的男人”,是脸部患病的爱德华(Edward)、整容成功后蜕变而成的英俊男子盖(Guy)、自信的奥斯瓦尔德(Oswald)。这三者是三个“不同的男人”,却也是“同一个男人”:丑而失败的自己、美而失败的自己、丑而成功的自己。
如果《某种物质》的自我关系是可怜的,《不同的男人》是悲惨的。《某种物质》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尚有曾经的辉煌;《不同的男人》一开始就输了,永远追不上的风口,宿命般的失败,如同结尾那句调侃:“我的老朋友,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尝过美貌甜头的伊丽莎白,让走下坡路的自己变得更好,当更好的自己反噬时,她有力回击,虽两败俱伤,但至少扳回过属于自己的部分局面。而同样容貌焦虑的男性,在《不同的男人》视角下,比女性更难堪和无解。男主可视作当下时代失败者(Loser)的化身:总是踩不到点上,总与“正确”擦肩而过,运气绝缘体,不仅追不上下一个红利,连到手的红利都丢失,拱手让给别人。
男主的名字盖(Guy)意思是“家伙”,隐喻他可以是随便哪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男主:跳槽后,新公司破产,旧公司崛起,旧同事飞黄腾达;失恋后,前任觅得良人,自己形单影只;出国后,国内迎来经济红利,自己却在萧条的异国漂泊。你为变更好做出选择后,却没有变好,而是更差了,你曾瞧不上的原地踏步者,只因运气垂青,就成了风口上的猪。更讽刺的是,所有决定,并非因为弱智和冲动,而是理性科学决策的结果,《不同的男人》甚至动用了高科技,一切看来正确完美。

《道林格雷的画像》(左)与《不同的男人》(右)
变成苏的伊丽莎白,再次受到大众欢迎;可变成盖的爱德华,仍不被认可,外界又把“不同的男人”奥斯瓦尔德作为他的新榜样。伊丽莎白嫉妒变得更好的自己(苏),而盖却嫉妒本来可以成为的自己(奥斯瓦尔德)。被苏暴打的伊丽莎白还能与苏同归于尽,可面对“不同的男人”奥斯瓦尔德的羞辱,盖却无能为力。眼看自己的原创不属于自己,成了别人的原创,还要在这位冒充者的援助下养伤、因他坐牢、出狱后蒙其关怀,并接受他与心爱女人结婚生子、功成名就的事实。

外形相似的“不同的男人”们 图:《不同的男人》

名字相似的“不同的男人” 图:《不同的男人》
除了三个“不同的男人”,影片还有相似却不同的名字:Edward与Oswald高度相似;Oswald与《道林格雷的画像》作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相似;爱德华在酒吧时,一位自称Guy Gaunt的男人说认识他,手术后的盖全名Guy Moratz;盖被同事问“你杀人了吗?你究竟是谁?”,同事更愿叫他法比奥(Fabiao)。一闪而过的人物也是“不同的男人”:外形高度相似的路人、自杀的邻居与被男主杀死的受害者,以及外表难辨的女路人、酒吧招待和表情悲伤的女人。
还有个更加“不同的男人”是邻居英格丽,一个掌握审美话语权、选角决策权、“拥有男人般权力”的女编导。她喜欢弱势男性角色,而非真实的男主本人;她对男主说“按我说的去做,这是我的创造物”,诚如一些喜欢控制女人的男人;她自称男人是“她诸多情人中被抛弃的一个”,与多伴侣出轨的男性相同,《不同的男人》也是性别倒置的隐喻。
平庸之恶:不求修改规则,只求更顺从规则
尽管电影关于容貌焦虑,隐喻的其实是绩效焦虑,是现代社会几乎无人能逃避的绩效标准:成功、优秀、年轻、富有;有房有车有娃;35岁应该如何,40岁应该怎么样……标准的制定者是掌握权力资本的一方,但资本主义的毒性在于,它极具迷惑性地偷换概念,让人误以为不达标准是个人责任,而非标准本身和标准制定者。
在极具说服力的“责任在你”说辞下,电影主角们对待规则的态度,不是质疑和反抗,更未试图修改规则,而是顺从迎合规则:用科技狠活整容,内卷自己以变更好看;盖甚至为迎合女编导而二次内卷,用面具把好不容易换来的帅脸遮住,从变帅改为扮丑。
电影主角们也是当下世界多数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资本、公司、权力和政治,显出“平庸之恶”本色。将外部PUA内化为自我内卷:责令自己要变更好,选择治疗过程十分痛苦的整容科技;为达标不惜犯罪和践踏他人:伊丽莎白制造苏这个工具帮她实现野心,苏又从伊丽莎白身上嗜血以葆青春,盖因嫉妒奥斯瓦尔德而去砸场,还将愤慨发泄到无辜者身上,走上杀人犯罪之路。

大衣、蛋黄、药剂都是黄色,代表人的物化 图:《某种物质》
在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当道的世界,平庸者往往不愿反抗和推翻规则,更愿在顺从规则的路上走得更远。修改规则难度大,也可能失败后一无所有;顺从规则、自我物化和内卷,却可能短期内取得更大效益:伊丽莎白通过科技分离出美丽的苏后,很快在娱乐圈再次成功;爱德华整容成盖后,马上成为地产销售冠军和形象代言人。伊丽莎白与盖的行为解释了平庸之恶的“合理性”:逃避可耻但有用,奴性有错却好用。推翻规则,虽正确但困难;顺从规则,虽错误但容易,平庸者更青睐后者。
理性选择失灵:没有美丑,只有谁在审美和审丑
虽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合理选择”,伊丽莎白和盖却都走上毁灭性结局,前者变成怪物,后者成了杀人犯,从丑变美,再到更丑,即“丑——美——更丑”的失灵之路。
平庸者的理性选择,为何失灵,导向毁灭?导演给出不同答案。《某种物质》的外界标准单一:只要更美更年轻的肉体,单一标准让内卷的人类无法负担压力并爆炸。内卷是虚妄的,因为达标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当娱乐公司老板对“曾是奥斯卡影后”的伊丽莎白嗤之以鼻时,问题不在女主,而在于资本秩序中不再有性价比的劳动力,其一切皆可被否定,被资本需要时她是美丽的,资本不再需要时她就是无用的,像女主这样获奖累累、功绩无数却被当垃圾丢掉的人,在绩效社会比比皆是。

制定“美丽压倒一切”规则的娱乐公司老板 图:《某种物质》
《不同的男人》的外界标准是变化的。男主不仅负担内卷压力,还在阴晴不定的标准前一次次落空:当他是爱德华时被嫌弃“太丑”了;变成盖后被嫌弃“太帅”了;新标准变成“丑而自信”后,盖再次戴上面具“扮丑”,还自信爆棚地满口吹嘘,却仍不受欢迎。《某种物种》迎合的是审美文化,《不同的男人》先迎合审美文化、后迎合审丑文化。前者认为追求美貌理所当然,后者揭露追求美貌并不理所当然,追求丑陋也合情合理,美与丑不存在哪个应该或不应该,一切取决于权力——权力追求美,美就是应当;权力追求丑,丑就是应当。在权力的世界,重要的不是美和丑,而是权力在肯定或否定着美与丑。

在两性关系中掌握权力、制定和修改审美规则的女编导 图:《不同的男人》
迎合标准的理性选择失灵后,如何面对毁灭性结局?《某种物质》虽没有修改规则,却带着制定规则者同归于尽。女主变成怪物,但叫嚷杀死她的老板和观众又何尝不是怪物?伊丽莎白是扭曲制度的强化者,也是受害者,这具怪物正是扭曲价值的视觉化呈现,伊丽莎白用将血液泼向老板和观众,用自毁的方式报复上位者。
《不同的男人》是一则更残忍的政治隐喻。出狱后的男主,发现世界不仅照常运转,甚至更加嚣张,审丑者与丑人相亲相爱。男主陷入巨大的虚妄茫然,正对应了当下的荒谬世界:顺从命运,可能是被歧视的爱德华,也可能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奥斯瓦尔德;主动改变,可能成为弄潮儿(在地产界大获成功的盖),也可能被时代的洪水淹没(坐牢的盖)。在兴风作浪的互联网、比特币、股票、出海、大厂和炒房热潮中,有人适时改变、飞黄腾达,有人同样改变,却只落得失败破产。人为迎合规则疲于奔命,还要被不断变换的规则当猴耍,这恐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权力的故意为之,是权力设计了一套让人永远不能达标的机制,而以男主为代表的平庸者,对此束手无策,无论迎合或不迎合规则,失败都是注定的。
更危险的物质
电影中一个容易被忽略,却最不该被忘记的细节,就是科技。比权力上位者更危险的,是掌握科技者,只是电影将科技的威力隐去了:《某种物质》的药物开发者是匿名的;《不同的男人》的药物研发者是未知的;《可怜的东西》的器官移植科学家古德(God),是待贝拉如亲生女儿的慈父式上帝。
电影编剧为保持故事主线,没有对科技做展开,但观众不妨大胆设想:如果科技开发者修改药物编码,《某种物质》不给营养液、改变营养交换天数、激活针失效,会如何?如果当权者知晓了科技的存在,即娱乐公司老板和女编剧得知男女主人公做过整形,或墨西哥黑帮知晓艾米莉亚其实就是前毒枭马尼塔斯,会如何?如果当权者也开始使用科技,例如女编导变相逼迫演员们去做科技整形,会如何?再进一步,如果当权者掌握了科技,娱乐公司老板买下了神药开发公司,又会如何?

整形科技 上图:《某种物质》;中图:《不同的男人》;下图:《可怜的东西》
所有设想,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当权者正在掌握科技,科技新贵已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权力之巅与特朗普联盟。更魔幻的是科技成长速度,远超人类学习如何使用它的速度,科技超前于权力,连规则制定者都无法驾驭科技。
除了科技,我们或许还能对剧情做另一种设想:主角不做平庸者的理性选择,不迎合规则,会如何?不整容的爱德华遇到奥斯瓦尔德,会不会获得启发,通过改变自卑而非容貌,获得快乐?伊丽莎白坦然接受老去,唾骂老板,离开公司,会不会更幸福?
2025年初始的真实世界,给了我们一个欣慰答案:拒绝顺从规则,不会万劫不复,仍能有所成就。《某种物质》女主扮演者黛米·摩尔,就在62岁的年纪获得人生第一个表演奖项金球奖最佳女主,“30年前有人对我说,我只是流量女星,只能演卖座赚钱的爆米花电影,我也真信了。这种想法侵蚀了我,让我觉得我不配当实力派,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黛米·摩尔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谈道。但她还是没有顺从规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成功、不够聪明,或者就是不够的时候,要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够,但只要你放下标尺,你就能看到自己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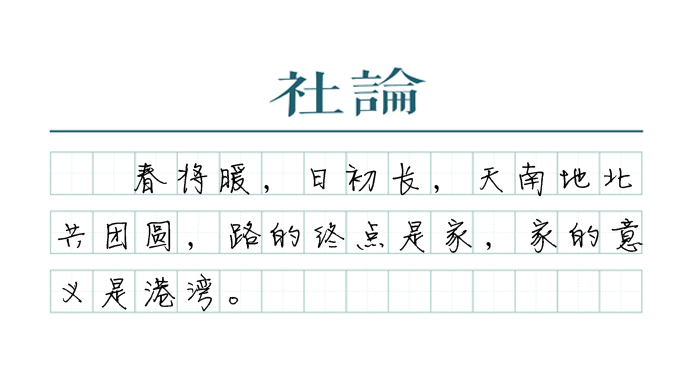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