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打开大门还应向前一步
- 资讯
- 2025-02-04 11:48:11
- 12
2024 年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与办公园区一墙之隔的北京理工大学。园区与学校之间设有一个出入口,午休时分,有不少和我一样的打工人,离开写字楼,到大学校园里走一走。校园里有一个标准的 400 米跑道,我在冬日的阳光下跑了半个小时。

20 多年前,我也在这个跑道上跑过步。那时我周末跟着一个叫绿野的组织爬山,为了锻炼体能,平日晚上,大家相约到北理工跑步。教学楼的灯光抬眼可见。已经毕业好几年的我,重新感受到大学的气息。
那时只道是寻常。谁也没想到,20 年后,一场疫情让高校关上了大门。去北大礼堂看演出、去浙大博物馆看展览、去武大看樱花、带孩子游览清北校园……过去这些我们当成常态的日子戛然而止。
疫情结束后,舆论一直在推动高校重新打开大门。经济观察报在评论《期待回归日常的这一年》中表达了这样的呼吁。那时,北大和清华刚刚宣布恢复校友进入校园的权限——很低调的一条新闻,也只开了一个小口子,但却令人振奋。我们在文章中表示,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更多高校打开校门,不仅对校友,还应面向全社会。随后,经济观察报在每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节点上都刊发了评论:《大学向公众开放应是常态》《高校开放,不妨更开放些》《期待更多高校打开大门》。
《给予大学生更多自主和自由》是针对 " 五一 " 长假前夕,一些高校对学生离校旅游设限的现象而写的一篇评论,批评当下大学的管理正在 " 高中化 ",同时也提到," 长期被诟病的大学校门的封闭,同样是这一管理思维下的产物 "。
现在回过头看,这种持续跟进和发声值得。在舆论的推动下,高校的大门在一点点地打开。很多高校发布了开放校园的通知,有的表示社会人员刷身份证即可入校,有的还保留了预约规定。
我们乐见这样的改变。这是对社会舆论的倾听和回应,也是公共政策和民间声音的双向奔赴。作为媒体,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有责任表达立场,推动改变。当然,我们的表达也恪守了 " 理性、建设性 " 的思考方式,立场鲜明,但拒绝情绪化。
站在现在的节点上审视,高校的开放已经完全回归到疫情前的常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些知名高校,开通了公众预约通道,但依然一席难求。我有一位同事,亲戚从成都来京旅游,想参观故宫和北大。同事通过官方渠道预约不上参观名额,又不希望大老远来的亲戚遗憾而归,她只好求助 " 黄牛 "。结果是,参观北大的 " 黄牛价 " 比参观故宫的还高。而高校向公众开放,原本应该是免费的。2023 年暑期,清华北大等名校研学热也引发了 " 黄牛 " 乱象。2024 年暑假,北京三、五、七年级的孩子想趁假期备战开学就要进行的体测,在社会体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想去家附近的大学操场训练。然而,他们发现,完全开放的高校寥寥无几。
高校打开大门还应向前一步。这并非不现实。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高校一直是完全开放的。我的母校是武汉大学,我自己就有过阳春三月夹着课本穿行于赏樱的市民之中的经历,也曾去隔壁院校找老乡,在他们的校园里夜谈到黎明。我一直认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公众在这种开放中都会受益。开放本就是大学应有的基因,大学不是象牙塔,大学生作为准成年人,正是在与社区的互动中学习如何走入真实社会的熔炉。
高校开放当然不是没有边界的,每一个进入校园参观的公众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但这是技术层面要探讨的话题,现在阻碍开放的,更多的不是技术而是观念。我们看到,一些高校学生对校门开放也持反对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公众参观时不遵守规则引起了反感,另一方面,很难说不是观念被习惯规训的结果——在校门封闭之下生活久了,会以此为常态,对开放反而难以接受了。
打一个类比,现在的中小学生认为课间十分钟不出教室天经地义,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们不希望以后人们对大学校门不能自由出入也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的大学时代都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正值寒假,大学校园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研学旅行的热门目的地," 预约难 " 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同事亲戚的经历不是偶然。如何更全方位地开放校门,高校还应该进一步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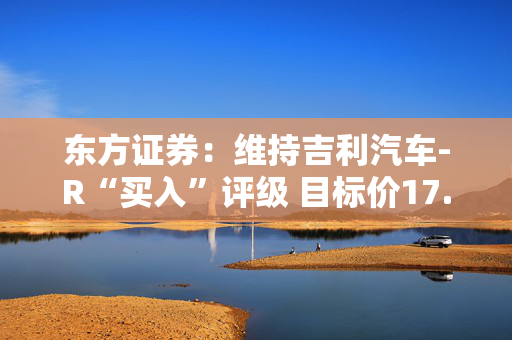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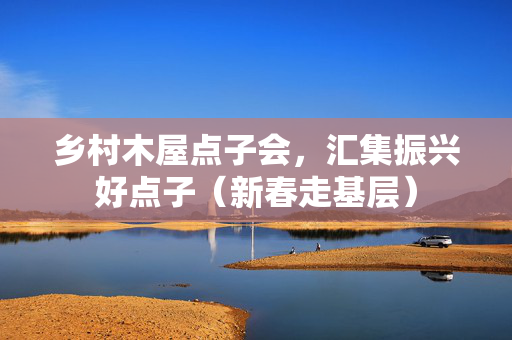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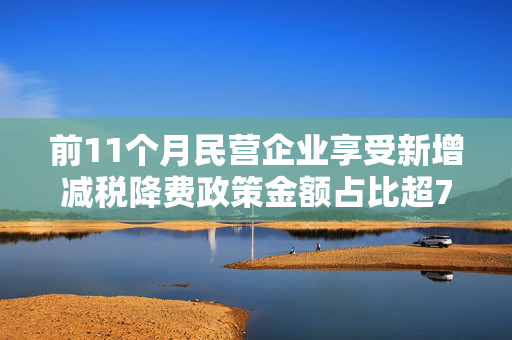







有话要说...